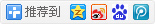十二岁那年,江瑗在自家姐姐的谢师宴上见到了一个睡眼惺忪的男人。 在这场谢师宴上,有人像是找到了喝酒的正当借口,一杯接一杯的灌着,有人像是从泥塘里挣脱之后的喜极而泣,但不管怎么样,每个人都是面带笑容。 唯有这个男人,睡眼朦胧的半躺在椅子上,说是“躺”好像还不是很贴切,准确来说应该是“瘫”。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旁边人说的话,反正他那眼皮就差那么一点就合上了。
每日推荐:初夏贺北溟全文免费阅读 , 李准穿越六皇子小说全文免费阅读 , 成为全校公交车的日常生活 , 宝宝腿再趴开一点就不疼了 ,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免费 , 尤物娇妻 , 花蒂被吸嘬的越来越爽 , 翁公又大又粗挺进了我 , 与你爱浓 , 腰窝H是酸甜PO